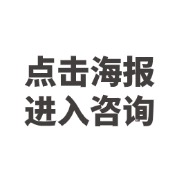原中国期货业协会兼职副会长 张宜生
有色金属期货是我国发展时间较长、公认较为成熟的期货板块,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长期发挥较好。同时,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长期稳定盈利和长期稳健经营能力也较为突出,行业供求关系、杠杆率、库存和成本等结构性指标长期处于相对较合理水平。现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进出口国,这当中期货市场功不可没。然而,由于资源分布特性,我国有色金属企业往往位于边远贫困山区。在这种恶劣的区位条件下,有色金属行业如何率先试水期货,又如何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个中奥秘值得我们细探究竟。
有色金属行业的体制变革
有色总公司的前身是冶金部下面的有色金属总局,是个政府机构。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把有色金属总局单独拉出来,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从政府先转成“政企不分”的企业化机构(代行行业管理职能),然后再转成企业,完全转成企业是在2000年。
有色体系品种很杂,很分立,有的品种之间甚至完全不相干。也正是由于有色体系的复杂性,它无法像石化系统一样实现高度垄断,市场化、国际化是唯一出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三角债”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它的市场化进程。
1985年,价格双轨制开始推行。双轨制之前,我们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我们的客户只有一个——国家,生产完国家就拿走了,也就是统购包销模式。但是计划经济有其弊端,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国家提出要改革,企业可以自筹资金上项目,上了之后产出可以按照市场价卖,不过国家要求的任务我们还要按照单子上交,这就形成了国家统配资源和市场资源双轨并存的实际状态。
双轨制下的市场价格暴涨,就出现了企业货币流动性不够,企业没钱支付不断上涨的高价原料,积累下来,“三角债”就出现了。1989年,有色总公司的东西开始卖不动了,卖了也拿不到钱,企业就不卖了,出现了大量的库存积压。于是,我向领导提出办交易所的想法,初衷并不只是为了“发现价格”,更多的是为了增加中间社会库存,让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持有产品,起一个“蓄水池”的作用。当时由于国家对铜、铝、铅、锌、锡、镍这6个有色金属大品种实行最高限价政策,看来看去,只有深圳特区对最高限价可以政策性突破,所以就选择了靠近香港的深圳作为兴办金交所的最终地点。在有色总公司的支持下,1991年6月10日金交所正式建立。有色金属企业在有色总公司的指导下愿意率先探索期货交易,则主要源于有色总公司的一步步引导和扶持。
第一,一些大型有色金属企业拥有金交所股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参与积极性。第二,帮助企业培养期货人才,解决了后顾之忧。第三,定期提供市场分析报告给有色总公司和各下属公司使用。此外,有色总公司还成立了多家期货公司和交割公司,服务企业期货交易。期货市场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间的信用体系,让企业更愿意采用期货交易方式。
期货市场让有色行业焕然一新
从1991年金交所成立,有色金属企业参与期货交易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1-1996年。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解决企业的瓶颈诉求,有色企业把期货市场当成现货集中交易的场所,目标是建立客户群,恢复信用,解决“三角债”问题。与此同时,发展期货市场的另一个目的是服务政府价格改革,对有色行业来说,就是确立行业产品的市场合理价格。
第二阶段是1996-1998年。这个时期企业开始普遍利用期货价格和运用套期保值,而不再以交割为主了。企业间物流配送开始出现,配送可以说是代表企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1998-2004年。这个时期我们的外贸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拿长单,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完成了从有色金属出口国到进口国的巨大转变。
第四阶段是2004-2012年。这个时期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市场上拿长单的主角。第五阶段是从2012年至今。这个时期有色金属期货市场库存很多都是私募基金的,这些私募基金已经介入有色金属期货市场,成为市场不可或缺的机构投资者,有色金属市场壮大了,同国际市场融合更紧密了,金融属性已经很明显。
经历了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后,有色金属行业已经从一个最封闭的行业成为我国最开放、最市场化的行业。
建设更好的市场为实体服务
回顾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当初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我们熬过来了。我们把提炼出来的风控精髓转化成管理理念与经营约束机制,培育成内部管理体制,沉淀为一种行业文化。这么多年来,我们再也难以看到有色行业的风险事件了,这就是进步。
但不得不说的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仍然有一些缺憾。为什么我们有色企业往往在国内市场做个5-6年,就开始转向国外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首先,国外的交易成本比我们低。其次,我国期货市场在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方面还有所欠缺,需要更多的视角审视我们的发展。最后,中国的金融没有扎根实体经济。因此,一定要有牢牢扎根在实业的人来钻研期货,运用丰富的金融工具,才能让期货更好地扎根实体经济,并同我们强大的实体经济一起,在发展中逐步建立我们应有的话语权。(摘自《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